廣告主到底應該付廣告代理商多少服務費才算合理? 廣告公司自相殘殺、廣告主貪便宜的心態來自哪裡?
時間﹕2002年4月30日PM2:30~4:30
地點﹕虹頂商務聯誼社
座談大綱﹕
近來,台灣廣告公司服務每況愈下,廣告主又要求媒體佣金攤開在陽光下檢查,到底廣告公司和廣告主在「付費」方面﹐應怎樣才算合情合理?
主持人﹕
寶僑家品總經理李彥
與談人﹕
泰山企業行銷督導黃凱旋
信義房屋企劃部執行協理周莊雲
4A台北市廣告業經營人協會理事長阮世聞
百帝廣告董事總經理楊淑鈴
聯廣副總經理陳玲玲
台灣電通副總經理陳榮明
李彥﹕今天非常高興能一起來討論「廣告主付費制度」這個既有趣又敏感的話題﹔其實付費制度的問題﹐一直存在台灣廣告界﹐過去幾年也產生許多爭議。這幾年景氣不好﹐問題愈來愈嚴重﹐從有秩序到沒什麼秩序﹐甚至很多比稿比到最後竟然變成在「比價」。
廣告公司究竟是要提供最低﹑最合理的價錢﹖還是創意服務﹖期望今天的座談是共識的開始﹐能開啟一條互相對談的管道。
阮世聞﹕我在台灣做廣告20年﹐我發現早期客戶較尊重廣告公司代理制度﹐現在因廣告主可能已經打破對付費標準的認同﹐所以產生很多後遺症﹐希望幾位廣告界的朋友針對這個角度去解釋﹑分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﹖
楊淑鈴﹕我先釐清廣告代理制度的重要﹐其實廣告代理制度有點像婚姻關係﹐如果法律沒有規定一夫一妻制﹐我相信很多人會非常高興﹐但是這會讓天下大亂﹔今天廣告界會有這樣的亂象﹐主要是因為制度不存在﹐這是第一個前提。
再來﹐廣告公司與廣告主的關係實在太特殊﹐不像一般的採購﹐採購很單純﹐程序就是開標﹑規格標﹐誰最低標誰就得標﹐很單純。但是廣告不是說﹐誰賺的錢多﹑誰房子多就嫁給他﹐那是種「夥伴」關係﹐我們在創造「價值」﹐很難放在秤子上去衡量﹐所以關係是錯綜複雜的。因此﹐廣告主必須先認定與廣告公司的夥伴關係是怎樣的﹐這是我希望廣告主能夠先瞭解的。
收費制度不透明
李彥﹕再聽聽廣告主的看法。那麼﹐泰山企業黃督導從廣告人出身﹐到變成廣告主與廣告公司直接接觸﹐請你談談這制度的變化﹐問題到底在哪裡﹖
黃凱旋﹕當我7﹑8年前還在廣告公司的時候﹐也是常常抱怨廣告主怎麼不尊重我們﹔後來轉換成廣告主﹐我有時候跟廣告公司是夥伴﹐引導我的廣告公司幫助我開發新產品﹐給我最好的服務。當我在跟公司內部同仁簽廣告量跟代理佣金的時候﹐我又感覺不像夥伴﹐而像是採購。我們董事長在外面或許也和其他廣告主討論過價錢﹐回來就會問我為什麼人家比較便宜﹐也就是這個直接印象﹕「我們談到的價錢為什麼那麼貴﹖」
我們在與廣告公司接觸時又少了評量制度﹐以我的角色來說﹐想要增加代理佣金連我都講不出來﹐但要扣款的時候卻很容易﹐這是廣告公司比較吃虧的地方。很多廣告主認為﹐目前收費制度多少有些不太透明的地方﹐代理佣金的部分還好﹐在媒體的部分更是嚴重﹐這也是大家最關切的問題。
周莊雲﹕我個人認為制度的變化﹐是因為產業經濟改變造成的。比如說以前是一家代理商﹐負責所有的廣告創意﹑媒體企劃購買﹔但現在媒體購買或分工更細的工作﹐都已經分出去﹐廣告代理商還能按照以前的制度收費嗎﹖我認為廣告公司應該從廣告主的角度來看事情﹐因為廣告公司大概是所有顧問跟合作夥伴裡面﹐和廣告主關係最密切的﹐所以我認為雙方立場如何一致化﹐是解決付費制度根本的關鍵點。
廣告公司無法賺錢
陳玲玲﹕我覺得最近一年有些變化跟往年不同﹐第一是現在很多獨立的媒體服務公司成立﹐這對廣告公司是一個蠻大的衝擊。另外﹐台灣有某些公家單位﹐總是用非常「低」的佣金要廣告公司來比稿﹐也是蠻奇怪的現象﹐這樣下去廣告公司完全沒辦法賺錢。
我做廣告也是一路披荊斬棘過來的﹐感覺現在的廣告公司比以前被廣告主要求的多很多﹔以前做廣告非常單純﹐拍完電視廣告﹑報紙廣告﹐大概事情就做完了﹐可是現在許多新媒體如網路媒體﹑手機媒體成立﹐廣告公司必須用一些新的思維跟方式﹐去為新媒體創造屬於它們的廣告型式﹔然後運用整合行銷結合公關﹑活動﹑手機媒體﹑網路媒體和傳統媒體的創意購買。廣告公司比以前擔負的責任更多﹐但利潤並沒有提高。
李彥﹕剛剛玲玲講到幾個重點﹐我們應該去察覺﹐或者應該認清時代真的有了很大的改變﹔如電視媒體自有線頻道竄起後﹐從以前的三台到現在的六﹑七十台﹐五花八門﹐廣告主有很多機會可以和消費者溝通。
現在廣告主的業績成長或衰退會影響到廣告公司﹐那廣告公司會不會像以前那樣﹐一味地把所有的預算打在電視媒體上﹐因為以前是照比例抽佣金﹐打多一點GRP(總收視率)就抽愈多﹐但這種制度已經沒有了。現在廣告公司跟廣告主是一種合作夥伴的關係﹐這個付費制度改了以後﹐我很明顯看到廣告公司有了改變﹐會用最好的方式去跟消費者做溝通﹐而不是把利益擺在前頭。
我發現大環境的改變﹐溝通方式增多﹐競爭也日趨激烈﹐就出現一些用很便宜的價碼要和你做生意的廣告公司﹐但仍有願者上勾﹔廣告主也面臨同樣的問題﹐他今天跟廣告公司殺價殺到一個他覺得「最低」的價錢時﹐老闆還可以從其他地方聽到「更低」的價錢。廣告公司或是4A有沒有努力過﹖現在的情況是﹐買方根本不知道賣方要賣多少錢﹐只是一直無謂地殺價﹐而且通常殺完價後都還覺得不是最便宜的價錢。
不尊重廣告代理
陳榮明﹕廣告公司代理制度是怎麼來的﹖我印象中以前廣告代理制度是媒體來想的﹐因為以前的廣告主沒辦法購買媒體﹐他不能跑到電視台說我要跟你買電視時段﹐或跑到報社說我要買版面﹐所以媒體才想到應該要有一個廣告代理﹐來整合這些廣告主的需求。
以前廣告主也沒有什麼行銷﹑創意或媒體的想法﹐所以廣告主也希望廣告公司有人才﹐可以幫他們解決公司內部的整合問題﹐因此廣告主覺得廣告公司幫我解決問題﹐應該給廣告公司錢﹐只是這個「錢」在當時的定義﹐是說廣告公司購買媒體的費用﹐媒體設定了這個代理制度﹐所以媒體跟廣告公司說服務費用是20%。我記得統一在兩三年前好像還是付20%的費用﹐後來因國際性廣告公司進來台灣後才改變。
廣告公司可說是專業的魔術師在生產一個創意﹐這個創意傳播出去﹐可以吸引消費者購買商品﹐因此廣告主應該尊重廣告人的創意﹐日系客戶到現在還是尊重廣告代理制度﹐也就是以17.65%來計算服務費。
以前產品行銷是廣告主要思考的﹐廣告公司負責傳播執行﹐現在客戶已經把廣告公司當作他們的人了﹐可是廣告公司的價值卻沒有因此提升﹔有些公家機構不尊重廣告代理制度﹐有些媒體直接跟客戶接觸﹐用專案的方式跟客戶談﹐把創意﹑企劃和行銷的價值完全分開了。
李彥﹕17.65%服務費的參考價值是不是已經不適用了﹖還有廣告公司的價值在哪裡﹖泰山和信義房屋好像有不同的看法。
黃凱旋﹕剛剛我一直在想價值的問題﹐我相信廣告公司是我的夥伴﹐可是再好的公司也有好壞﹑高低起伏﹐因為廣告公司的團隊素質不同﹐對產品的熟悉度也不同﹐像飲料業是台灣消費品競爭最激烈的行業﹐成功率也許10~20%。
今天廣告公司給了一個很好的創意﹐讓廣告主的產品成功了﹐1年產品賣了新台幣10億﹐可是沒辦法分給廣告公司﹐如果今天產品失敗了﹐廣告公司還是我們的朋友。
不過如果產品失敗了﹐還收17.65%的服務費﹐老闆可能就會開始想﹐當初有印象15%﹑13%﹐甚至10%﹑8%都有﹐每個廣告主都有適合的環境﹐所以廣告主該找怎樣的廣告代理商﹐完全看廣告主的選擇。我們很不希望東西賣不好﹐老闆指示重新比稿﹐我相信是每個行銷經理及廣告代理商最不願意聽到的事情。
廣告代理價值大不如前
周莊雲﹕就整體而言﹐現在整個市場的費用都在往下走﹐我想有幾個原因﹔第一﹐現在的媒體及溝通環境很複雜。第二﹐現在行銷及廣告的分工愈來愈細﹐到底廣告代理商是否因為這樣的分工而有所轉型﹖就我觀察﹐轉型似乎還沒那麼順暢﹐廣告代理商的核心任務到底是什麼﹖有沒有配合廣告主的需求做改變﹖另一方面﹐也因為台灣經濟發展和資訊更發達﹐廣告主的能力或本身品質也有上升﹐所以對廣告代理商的要求會更不一樣。總之﹐廣告代理商的價值似乎大不如前。
就個別面來看﹐我個人相當認同的是﹐個別廣告主和廣告代理商之間﹐本來就有合作及交易的行為﹐彼此間自然會產生一種收費方式﹐但是﹐假如廣告代理商提供的價值比較高﹐相對地就可以要求較高價格及收費。
李彥﹕有關轉型的部分。早期廣告公司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個專家﹐也就是用17.65%來算﹐但現在很多廣告主﹐都有自己的行銷部門﹐可以參考價錢的。行銷部門及媒體都在改變﹐以前的「菜單」現已不適合﹐才會導致大家的反彈﹐想要自行訂定「菜單」﹐我們是否有必要來討論出一個新的「菜單」﹖
阮世聞﹕剛剛我們有兩個不同的看法﹐一個是價值﹐一個是價格﹐如果客戶和廣告代理商不幸決定一個機制﹐我們是15%還是17.65%﹖把它規定以後才去評估價格﹑價值﹐如果現在價錢談妥﹐卻發現價值是不夠的﹔如果全世界公定是17.65%﹐那事情也就好辦了﹐廣告主只要找出一家最好的廣告代理商﹐再來看他的價值便可決定。
如果反過來﹐先定好了價格﹐再去談價值﹐還是會有廣告公司夠不夠專業的問題﹔其實﹐只要讓廣告代理商講三句話﹐就可以知道這家廣告公司有沒有「料」。如果廣告主的窗口不是很專業﹐又要對老闆交待﹐廣告主方面就會沒辦法維持廣告代理制度了。
李彥﹕17.65%的服務費是純粹給廣告公司﹐還是有一部分給媒體﹖以前我們公司在付17.65%的服務費時﹐15%是給廣告公司創意方面﹐2.65%是給媒體。現在的廣告量很大﹐跟量很小的時候花費的人力不一定差很多﹐尤其是創意方面。17.65%不是以量多或量少來計算﹐就會變得不很公平﹐所以廣告主就會談佣金的比例﹐甚至自己去跟電視台談。
阮世聞﹕這就是最原始的狀況—沒有制度。如果廣告代理制度被硬性規定的時候﹐媒體自然就會有個制度在﹔如果大家都有共識﹐都了解廣告代理制度是怎麼回事﹐大家合作也比較容易﹐但這也是最困難的部分﹗
李彥﹕所以﹐現在面臨的問題是﹐不管電視或平面媒體﹐因為制度的不透明化﹐所以也沒有辦法訂出讓大家遵從的付費制度。而創意制度上﹐怎樣的方向才比較正確﹖
阮世聞﹕廣告量很大的時候﹐價格上應該要有所優惠﹔其實﹐我在台灣做廣告20年來﹐可以說沒有一個客戶的量是大的﹐只能說全部加起來很大。像麥當勞和P&G﹐有20幾個廣告策略﹐但一個策略平均下來也只有新台幣幾千萬而已。
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場
李彥﹕我覺得你這樣講很有道理﹐因為以廣告活動來算的話﹐尤其現在廣告的生命週期已經愈來愈短了﹐以前一支廣告可以播一年多﹐現在一季可能就要播三支廣告。
楊淑鈴﹕因為早期媒體付給廣告代理商的佣金是整體的20%﹐等於是淨利的25%﹔20年前﹐國際性廣告公司進來台灣後﹐把美國整體的15%觀念帶進來﹐台灣廣告公司的佣金跟著往下降﹐一下子變成17.65%﹐台灣的市場規模很小﹐而且有些製作費廣告主是不付的﹐所以台灣的廣告公司經營比美國還辛苦。
但如今媒體公司成立﹐佣金中有多少比例給媒體公司﹑多少給廣告公司的創意部分﹐坦白說﹐是這兩年才思索的問題。以前廣告公司有媒體部門﹐經營者看報表一目了然﹐也許媒體只要1%或1.5%就可以操作了﹔但現在媒體已獨立出去﹐他們也要有利潤﹐經營成本相對變高了﹐原本的百分比沒辦法滿足他們﹐該付給媒體服務公司2%還是2.57%﹐這都是這幾年來面臨的問題。
也因為這樣的環境﹐廣告公司的定位從「綜合廣告代理商」變成一個「創意代理商」﹐我認為我們不只是創意代理商﹐而是創立品牌的代理商﹐我們從市場的方向﹑定位﹑機會﹐找出操作品牌成功的模式﹐一路下來﹐我們付出也很多。不管是哪種付費方式﹐前提是如果廣告主尊重廣告代理﹐大家都公平公正﹐合作方式其實蠻多元的。
李彥﹕從廣告主的立場﹐黃督導覺得這樣的說詞﹐能不能說服你們對付費制度的合理性及必要性重新思考。
黃凱旋﹕整個付費制度要回到交易制度來看﹐我願意用多少錢買你的創意﹔統一﹑金車﹑P&G這些大廠商﹐他們長期付較高的代理佣金﹐很多年甚至超過17.65%﹐這不是我們做得到的。
大客戶付較高的代理佣金﹐小客戶預算較少﹐所以廣告公司代理佣金少收也就做了﹐這樣到底公不公平﹖大廠商「量 」那麼大﹐卻付了更多的代理佣金﹐但可能也有很好的品質﹐可是我比較相信的是﹐當客戶的量大時就該有更多的服務﹐也許是價錢上的折扣﹐這是個很基本的觀念。
我覺得交易部分有大致的水平﹐權利與義務也有分級制度﹐但在這付費制度下﹐我仍不知要盡多少義務﹑享受多少權利。
周莊雲﹕其實廣告主的量到了某一個程度以後﹐17.65%就該調整才較合理。為什麼廣告主和廣告公司會有對立的情形﹖假使說這波廣告預算少一點﹐廣告代理其實花的力氣差不多﹐但所得比較少﹐這時廣告主不會有意見﹔如果廣告主要花多一點的媒體費﹐其實廣告公司花的力氣差不多或沒有多太多﹐但廣告主要多負擔費用﹐這時便會有爭議。
我在想﹐為什麼每家廣告公司的收費方式跟比例會有那麼大的差異﹖會不會是廣告業結構上的變化﹐讓中小型的廣告代理商願意接受較低的費用﹔而廣告主又要如何區分價格和價值﹖產業面臨較大的變動時﹐主流業者又要如何提升價值﹖
創意不是數學
陳玲玲﹕創意不是數學﹑不是化學﹐也不像律師﹔創意會變魔術﹐也許廣告只看一遍就一輩子不會忘﹐也許看了一百遍還是記不起來﹐價值就差在這裡。我非常不以為然的是﹐有些客戶好像在買螺絲釘﹐或者把梵谷的畫用秤來秤—他不看畫的內容﹐他只看紙有多重。
我自己做過一個廣告策略﹐創造了話題性﹐雖然廣告費花了新台幣7千萬﹐可是廣告被媒體報導的價值﹐依出現的版面換算成廣告的話是5千萬﹔這就是「價值」﹐我沒有向客戶要錢﹐因為那是我們創造出來的。我也不認為廣告該擔負起銷售最後成敗的責任﹐因為廣告其實只是在「溝通」﹐當商品不好的時候﹐我們也沒有辦法改變。
評估一個廣告﹐要看廣告知名度是不是創造得很高﹐廣告偏好度是不是很高﹐消費者看完廣告想要買商品的慾望是不是很高﹐我甚至不同意用銷售來評估﹐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擔負產品好不好﹑通路好不好的責任。
Fee-base(廣告公司用了多少人力來做廣告﹐就向廣告主收取多少服務費用)是個好方式﹐但有個條件是﹐客戶要很清楚今年要做什麼﹐要跟代理商說今年我有三個廣告策略﹑三支廣告片﹑幾張平面稿﹐我們大概會以使用人力的薪水換算他花費的時間﹐算出一個非常透明的價格。但當廣告的知名度﹑偏好度都非常高的時候﹐請你再加一點錢鼓勵廣告公司﹐這是我個人認為最好的方式﹗
創意才是價值
陳榮明﹕電通不是用fee-base﹐是收服務費(Service charge)的方式。我想是整個環境的問題﹐日本人來台灣看到媒體的定價都很驚訝﹐媒體為什麼會有定價﹖買1億的媒體時段跟買1千萬的媒體時段﹐對廣告主而言﹐付出去的價錢是不一樣的。日本媒體是沒有定價的﹐日本媒體在同一時段對A客戶開的價錢﹐跟對B客戶開的價錢﹐是不一樣的。
廣告公司的價值是「創意」﹐我們的任務是把消費者「釣」到店頭﹐廣告公司的任務就結束了﹐廣告主要付的是創意的費用﹐至於「預算多折扣就要愈多」這個問題﹐應該要留給廣告主跟媒體去談﹐不是跟廣告公司談﹐我們沒有這種資格。
我希望廣告主多給廣告公司挑戰﹐前十大廣告公司也都在思考「如何不讓客戶跑掉」﹐我們賺的是智慧的錢﹐希望媒體能正視這個問題。
不能再惡化下去
李彥﹕我覺得要把台灣廣告主協會2A的立場講清楚﹐2A希望今天能有個開啟雙方對談的機會。
我發現不論是以17.65%或20%來收取服務費用﹐至少現在感覺到這是一個可以協調﹐可以討價﹑議價的市場﹔雖然廣告量愈大廣告主付費愈多﹐但是代理佣金也是可變的。當然每家廣告公司營業成本都不同﹐不應該為了保住市場而苦苦議價﹐營業不佳的廣告公司就被市場淘汰﹐而有些淘汰也是好的。
的確﹐要以廣告公司的表現來付費﹐是必須有一定的水準來認定的﹐因為一個產品的成敗跟很多方面都有關係﹔產品如果本質很好﹐但是如果定錯價格﹐產品就完蛋了。
過去兩三年市場不景氣﹐大家已經開始在代理佣金上動腦筋﹐最主要的原因﹐應該說是廣告公司願者上勾﹐可能5%的服務費才是對的﹐可能過去賺的都是暴利﹐我不知道。廣告主真的花較多費用在媒體購買﹐這又牽涉到佣金﹑價格不透明的問題。
代理佣金的問題有必要再討論﹐也許4A要有自己的立場﹐或者有必要將廣告代理商分級﹔希望大家正視這個問題﹐因為如果台灣廣告界再繼續惡化下去﹐真的無法想像沒有廣告的世界會是如何﹐一定很黑暗。(動腦盧盈君﹑吳睿淳錄音整理)
《資料來源:動腦雜誌314期2002年6月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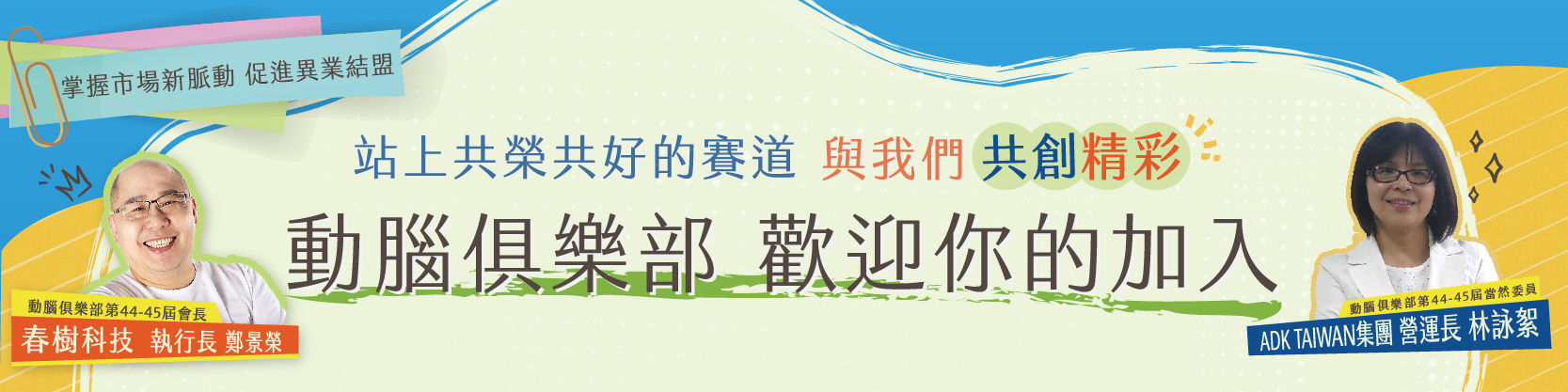




.png)